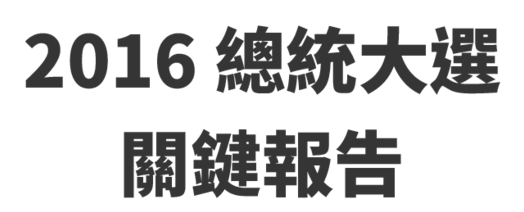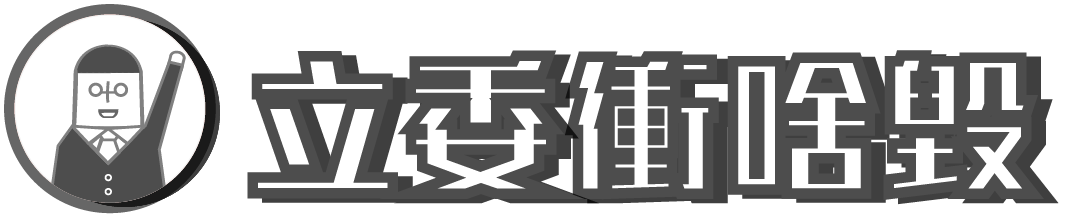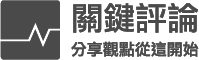國會改革兩黨吵翻天!新一屆立委該怎麼改革國會才能解決亂象?
文:關鍵評論網 鄭少凡
去年10月28日,正當10月中國民黨臨代會「換柱」餘波仍蕩漾,國民黨中常會提案建議修改不分區立法委員提名辦法,讓不分區立委且任立法院長,連任不限屆數,為原本受限只能連任兩屆不分區的立法院長王金平解套,而黨主席朱立倫也順勢提出國會改革的主張,此舉引發了國、民兩黨選前對國會改革的爭論。
國會改革不是新議題,從第七屆立委(2007年)開始時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都會邀請各黨派立委簽署國會改革承諾書,但國會改革法案幾乎都還是被擋,而在即將換屆的會期末突然提出國會改革,時間點確實令人質疑,民進黨立委隔天則召開記者會痛批,過去民進黨提過16個國會改革法案,包括議長中立、國會調查權等,但通通被國民黨團擋在程序委員會外,累積高達851次,並質疑朱立倫國會改革的動機是選舉考量。
國民黨也不示弱,隔天立刻還擊,指出民進黨這屆杯葛議案多達2655次,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李貴敏諷刺,民進黨應該先合法、理性問政,再來提改革。
之後兩黨在立院提出各自的國會改革版本,國民黨則是主張:國會議事效率化、協商透明化、議長中立化;而民進黨則是提出8大類別,包括憲法、法律及立法院內規等3個層級的黨團版本草案,包括18歲公民權、廢除監察院、落實單一國會、立法院正副院長退出政黨活動、黨團協商轉播、打破議事轉播藍畫面等。
不過在12月在黨團協商中雙方僵持不下而不了了之,國會的改革只好等到今年新的立委上任後才有機會。
 Photo Credit: 中岑 范姜 @ Flickr CC By SA 2.0
Photo Credit: 中岑 范姜 @ Flickr CC By SA 2.0
國會歷經的三波改革
國會是立法、審國家預算的最高機關,一舉一動都跟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但弔詭的是,立委普遍在人民印象中大部分都是壞的印象,到目前為止,立法院經歷過三波改革,第一波主要是在1999年1月第三屆立法委員任期結束前,立法院分別通過《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議事規則》等四法。
其中,現在被詬病的「黨團協商」就是這個時候正式被賦與法律地位,但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0條規定,「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全程錄影、錄音、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但從來沒有人見過這份「公報」,因此黨團協商被譏為「密室協商」。
第二波是在2001年之後第五屆立法院所進行的改革,主要針對黨團協商所引發的問題進行改善。
由於黨團協商後來演變成為凡有爭議或甚至來不及處理的法案全部都送協商,架空了委員會的功能,所以這波改革則將協商範圍限縮,增加「逕行二讀」設計,也就是委員會可以將審查完畢且爭議不大的法案直接送入二讀,不需送協商。
由於第一、二波的國會改革並沒有完全改善立法院的功能,國會的亂象依舊,立委的素質參差不齊,於是,在政治人物以及民意的驅動下,第三波改革從立法院的議事與組織,開始轉移到選制的檢討。
2000年開始,「立委減半」運動應運而生,經由民進黨政府的主導在2005年完成修憲,並且搭配選制的重大變革,由原本「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改制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式),並從2008年開始實施。
►相關報導:政問第六集》國會改革懶人包,帶你一次看清立法院25年來三波變革
直到現在,觀察兩黨提出的改革議案,有共通的一點,那就是「黨團協商透明化」以及「議長中立化」,黨團協商不透明而被批評密室協商,雖然法律規定要錄音錄影記錄在公報,但實際上都沒落實,而議長中立化,在2013年的九月政爭,更是成為討論的焦點。
國會改革到底出現什麼問題?TNL專訪了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現任台中市法制局長陳朝建,以及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陳長文,以他們的角度來解析國會改革到底要怎麼改比較好?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1月16日進行景觀法初審。攝影:陳文姿。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1月16日進行景觀法初審。攝影:陳文姿。
陳朝建:為人詬病的是國會運作的慣例
陳朝建:國會要改革分成形式的改革跟實質的改革,兩黨提出的國會改革細看差異不大,同樣都是協商透明化,同樣都是議長中立化。
若真的要看出差異的話,要看實質的部分,雙方都有共識,現階段國會最大的問題叫密室協商,雙方隱喻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國會經年累月都是同一位議長,國會議長借由黨團協商已經形成了密室政治,換句話說,國會要改革,一個是制度的,也就是法案的、制度化的部分,另一個就是「人」的部分,人選若沒調整,沒有互動新的模式,那也奢談改革,所以二月一日新的國會改革勢必會上路,即使沒有新的國會改革的法案。
因為早年國會改革有國會改革五法(《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議事規則》),早就通過了,已經實施多年,但是有關協商透明化、議事透明的部分,是聊備一格,像是黨團協商雖然都有條文規定要透明,但都沒落實,所以關鍵是在於人,而不是法案制度。
我做過研究,在「形式上」我國國會透明程度跟歐美相差不多,只是沒去落實法律而已,所以為人詬病的不是國會改革的法案,而是國會運作的慣例的問題。
新國會有新的運作模式
1月16日這場選戰已為2月1日的國會改革注入了新血,這潛在的契機一方面是太陽花學運引起的,另外是朝野在席次上會有劇烈的變化,國會議長、副議長勢必要改選,到時候就可以互動出新的模式,這新的模式預判上是過早了些。
舉例來說,王金平可能不是下一屆的國會議長,王金平模式就叫面面俱到,會不撕破臉,會跟在野黨間維持微妙的平衡,這就無法讓馬英九的意志貫徹,所以發生過九月政爭,政黨協商就是黨團的召集人跟議長享有比較大的權限,所以柯總召(柯建銘)也長期分享到這樣的資源。
將來這情況會有改變,也許幅度不大,舉例來說,假使柯建明是新的議長,搞不好是另外一個王金平,但有可能是其他人擔任議長,總之二月一日有戲看,不只是議長、副議長改選,還包括朝野間結構的重組,朝野間互動的形成,那自然跟協商的透明化有關。
像是「議長中立化」,理論上可以用修改法律來規定,但在現有的制度下可否用慣例來規定?可以啊,像英國國會不見得會規定議長要中立,是英國國會議長由最資深的人擔任,擔任議長後要退出政黨即政黨活動,我們長年以來的慣例就是不中立,那是因為他是多數黨的領袖之一,甚至是政黨中常會成員之一,這要用法律還規範不是不行,可是可能會出現一個現象,法律規定後表面上退出政黨活動,但實際上還是參加政黨活動。
要引進立法計劃
另外,如果是跟制度真的有關的改革,我覺得要引進立法計劃,就是限期討論、限期協商、限期表决,也就是說在一定的時間內討論,討論不成在一定的時間內協商,協商不成就是要限期表决,現在是協商不成未必限時表决,所以制度如果要改就是這一點,這樣國會改革才有辦法真正上路。
 Photo Credit:VOA Public Domain
Photo Credit:VOA Public Domain
陳長文:立法杜絕關説司法,這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國會改革?
陳長文:兩大黨(國會改革)的「意見」也許很好,我目前沒有細究他們對於每一項主張的細部做法,但重點是,期待他們「做到」的「可能性」有多高?
我在文章中曾提過:「國會改革最關鍵的其實是二件事,一是『賦予關說司法刑事責任』,一是『打破密室協商』。」
先談「賦予關說司法刑事責任」,2013年九月王金平院長爆發了關説司法的風波,從當時公布的監聽譯文來看,套一句當時的話「這不是關説,什麼是關説?」
再看一下法律,我們的法律對於國會議員關説司法竟無法可罰,完全得靠「立法委員」自律,我們能期待立法委員自律嗎?關説司法,在許多民主法治國,都可以説是「犯了天條」,但在台灣,卻可以雲淡風清,這是一個如何落後的法律?
然而,二年下來,只有黃世銘被辦洩密判刑定讞,但立法委員關説司法的刑事賦責卻無人聞問,事件過後,立法委員完全不打算修法賦予關説司法刑事責任,彷彿要刻意把這個「後門」開著,而台灣人民竟也不以為意,任由這個關説司法的後門徜開。這也是這些立法委員肆無忌憚的緣故。
説起來,立法杜絕關説司法,已經是對立法委員行為要求的最最低標了,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國會改革?
讓小黨有空間,製造更多競爭
我理想中的國會是,自律的國會,這包含理性問政;才德兼備或至少德勝於才;該反對的反對,但該支持的也要支持;能超越黨派與個人利益。當然,這叫「烏托邦的國會」,陳義極高,但這就是我希望的國會。
只是,這個陳義極高的理想國會,無法只靠自律成就,仍必須有他律的作用以及制度的導引。讓小黨有空間,製造更多的競爭,可以增加大黨的進步壓力;聯立制,讓不分區的比例提高,可以平衡現在國會過度重視地方,致令國家弱化,失去領導力與方向感的困局。打破秘室,則可以讓人民知道,那些人要為那些法案的卡住負責,增加民主問責,讓立法委員不敢懈怠胡為。
不開除幾個大黨立委,他們怎麼會得到教訓?
我曾在文章中建議,「不分區立委席次按比例分配,只要把原來投給兩大黨的票,拆給新興政黨,使其超過5%,就有機會一舉達到教訓主要政黨、換血與制衡未來最大黨的三大目標。」
人民才是民主之本,國會表現不好,投國會一票的人民,不會沒有責任的。國會裡劣幣充斥,那人民就要用選票去淘汰劣幣,就算一時不一定代表新進入國會的就一定是良幣。但至少,把現有的劣幣淘汰,給予警惕,這就是一種進步。這是為什麼我鼓吹政黨票投小黨不投大黨的緣故,因為,大家如果不滿意二大黨的國會表現,你不開除幾個大黨的立委,拿掉他們幾個席次,他們怎麼會得到教訓而調整做法呢?